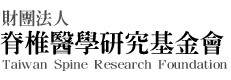台灣脊椎外科之父陳博光
前言
今天(2007年1月26日),我在大家的祝福下,即將卸下在台灣大學醫學院及附屬醫院的教職工作。與台大醫(學)院之結緣、打從我剛進到醫學院當學生迄今,算算也有四十七年以上的時光。我的青春、我的夢想、我的成長與成熟,到後來的蛻變,可以說一切的一切都與這所醫學院和附屬醫院息息相關。我多年的工作,大多數是教育下一代的醫生與醫學生和服務生病的普羅大眾。近二十年來對患有脊椎毛病的患者,更是我行醫的重心。
在這臨別之際,自然充滿著些許不捨,但是也載有愉快的心情離別。也就是說:「酒店關門了我就走」的情懷,就這般輕鬆瀟灑的告別這所傳統的學院。當年年輕時我帶著憧憬、仰慕的心情而來,現在我將以驕傲、無愧地告別我的母校。為此,我將簡述在這段不算短的歲月中,在我身邊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做為贈與後輩們離別的禮物。畢竟相聚是短暫而離別是永恆的,而且人是時光的過客、萬物之逆流。
一、生長與青少年時期
我出生在珍珠港事變後一年(1942年12月),這時的北半球,到處是戰爭、狼煙峰火四起,同盟與軸心國之間,為了爭強鬥狠,在歐亞大陸及三大洋之間,已爭相殺伐、兩不相讓之地步。在這段時間出生的人,真是生不逢時啊。
我瘦弱的身軀,父母親認為難以在北方寒冷的日本生活,遂決定一起返回台灣生活,畢竟台灣地處亞熱帶、氣候溫熱,比較容易讓人接受。也因此我們躲過了1943年春之名古屋大空襲,我這條小命方才得以延續到現在。
家父在桃園的鄉下開始行醫才一年多,又被日本政府徵召去南洋當醫官,這一去又是離別二十個月,世界大戰結束,家父還被關在印尼的戰俘營,直到1946年6月才得以返回故里。我和大弟差一點就當孤兒了。那段戰爭隔絕的期間,爸爸的音訊全無,母子三人過著不知所措的苦日子。
1948年進入國民小學,那時台灣仍然是戰後物質匱乏、生活簡樸的年代,但我很幸運有一個溫暖的家庭,讓我能夠安穩的求學。我從一個僅會說日語的小孩,蛻變成僅會說國語與客家話的小男孩。十三歲那年,幸運的考上了省立新竹中學,當時那是一所新竹地區人們心中的一流學校,但我雖然能升上這所十八尖山下的好學校,可我是倒數第二名考入的幸運兒。
中學六年,都寄居在山腳下的學校宿舍裡,當年沿用日本人的稱呼叫它為「學寮」。這兒住著初一到高三的上下級同學、他們有說客家、說閩南、說國語及阿美族各式語言,好像聯合國。可又是有軍事管理的味道,每天六點起床,分配任務,打掃庭院及廁所,大部份的人則到學寮下的大運動場跑步,然後一起吃三餐飯。當時的校長又是高舉德、智、體三育並進的辛志平先生。運動與美育是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活動。
經過六年的磨練,可是把一個瘦小的鄉下小孩,變成了一個非常耐操的少年人。這或許為我將來當外科醫師,能吃苦、終日為病人手術而毫無倦容打下了基礎的原由。能在聯考甲組中幸運考上台大醫師,居然獲取第二名「探花」,真是連自己都意想不到。反正,在中學之後到大學求學階段,我都是與「第一名」無緣,這種退而求其次的老二哲學,說真的倒是相當不錯,讓我輕鬆的交到很多朋友,這些朋友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中、都給了我非常多的幫忙,沒有這些友誼,我的人生有許多的困境是不容易排除的。
六年的醫科學習及第七年的實習醫師生涯,對我而言,實在蠻累的,要到當了骨科醫生很多年後,才真正知道這些骨頭解剖名字是什麼意義,這些肌肉又代表著什麼功能。反正考試到了,就儘量去背這些拉丁文或希臘文的解剖名字,其他基礎醫學各科也都差不多囫圇吞棗地應付過去,我常在想,當年外科學成績唸得不太好,要怎麼竟然當外科醫師?造物者啊!您是要我在餘生中常常要補習外科嗎?幸運的我竟沒有留級,也沒有補考過。
在南部當兵的日子,固然輕鬆愉快,但回到母校當住院醫師是從R2開始當起,我的R1生涯是在台北榮總,那一年也是過得蠻紮實的。一些由大陸來的國防醫學院前輩醫師們也都是一時之選,這些經歷無形中、讓我沒有門戶之見。反正,好的醫師到那裡都是好的,永遠都值得我們學習。當年一起工作的榮總住院醫師,現在都已任職各大榮民醫院的大院長,讓我深感與有榮焉。
二、住院醫師生涯
回到台大醫院外科擔任R2工作,說實話,要我馬上做gastrectomy實在不容易,我可是懷著忐忑不安之心在做。幸有學長們以親切的態度在指導,這種融洽和諧的氣氛,是台大外科住院醫師的一貫傳統吧。尤其是在林天佑主任的強勢領導下,更加珍惜這份寶貴的學習之旅。在外科工作的頭幾年,因為在各個病房輪值、有機會向很多師長們學習各種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的方式。也因此有機會,親自施行各種手術,比如胃切除(胃腸道疾病切除)、開胸、開頭顱的急診手術、以及各種病患手術的照顧等等,讓我有機會深深體會到各疾病的診斷、心肺的變化、和電解質平衡等問題。手術技術也逐漸成熟。這些都是教科書上所沒有的,而必須親身體會和思考的工作,這對我以後面對複雜的疾病和困難的照顧。都有很大的幫助。
當總醫生的第四年,我毅然決然選擇了骨科,病房在一西病房,當時共只有病床51床。由陳漢廷教授領導有四位的主治醫師,當時劉堂桂教授人在國外進修,另外接受了陳漢廷教授、陳博約教授、韓毅雄(講師)、陸永熙(講師)等四位老師的指導。當時常見的疾病仍以骨折、脊椎結核、小兒麻痺後遺症、頸腰椎的退化性疾病為手術治療之最大宗。
西元1972-73年間,當時人工關節在台灣尚屬萌芽階段,手術器械以及人工關節仍屬草創時期,即使在美國也是剛起步不久。因此我的訓練大部分集中在脊柱的前方和後方的手術技巧,還有骨折的整復,以及小兒關節畸形的矯正。
陳漢廷教授素以嚴格出名,令人敬畏,但他在手術技巧的明快、流暢和嫻熟方面令我獲益良多。陳伯約教授對病情反覆思考及精益求精,也是我相當敬佩的師長。韓毅雄老師則剛從美國學成歸國,他帶回生物力學的新觀念及骨折治療的方式也讓我耳目一新。陸永熙老師常常把病人讓我親自操作,令人愉快。
每週末的上午,陳漢廷教授查房要求、病歷要詳實、清晰並把使用的藥物、X光的描繪要求務必做到精確。讓所有學習的年輕醫師感到膽戰心驚。因此,總醫師的另一項任務就是安排門診後,利用下班空檔以一頓美酒、美食來彌補工作一周的辛勞和身心俱疲,這也許是我們做醫師的一種消除壓力的好方法之一。
可惜陳漢廷教授英年早逝,令人深感惋惜。回憶當年他生命末期和師母一起到芝加哥旅遊,和我曾有一短暫接觸和相聚,我親自得到二位的耳提面命和鼓勵有嘉,致使讓我對學術生涯的規範有了更明確的方向。如今事隔二十餘年,每念及當時情景,心裡總免不了是不勝噓唏。
三、礦工醫院的生活
總醫師訓練結束,因緣際會到礦工醫院。當時八堵礦工醫院設立於1953年,成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當地煤礦工人做保健以及治療,由勞保局輔助台灣區煤礦工會設立一家社團法人醫院。可以想像當時的病患是以外傷病人居多,因此院長一向都由台大出身的骨科醫師接掌。
有一天,我的同學黃振成醫師(心肺外科總醫師)騎著機車載我由縱貫公路來拜訪當時的院長陳永振醫師,在他誠摯又熱誠的要約下,我答應到礦工醫院任職並擔任副院長乙職工作(當時黃振成是外科主任、龍志強是泌尿科主任)。事實上,這家醫院的設備非常簡陋,雖是麻雀雖小,但五臟不全。記得我當時年少輕狂,且懷著滿腔熱血和理想,願意到偏遠郊區服務。
礦工醫院位在八堵地區,主要是以勞保的礦工和眷屬們為服務對象,或者是重大交通事故和礦工爆炸損傷都是當時治療的主要工作,而復健工作在當時也格外顯得重要。
不到半年的時間,陳永振院長遠赴日本進修,因此醫院大小各種責任都落在我的肩上要我承擔和負責,真是「小小的蚱蜢舟,載不動幾多愁。」我要負責醫療、醫院收支平衡(當時是負債)、各種醫療糾紛、以及穩定醫療人員員工的情緒和招募醫護工作人員、擴編醫師陣容等等繁瑣及複雜工作,真是強人所難啊。幸運的是,三人小組的犧牲和奉獻打動了當時煤礦工會顏、李二位董事以及詹總幹事等人,給予精神支持,才得以把醫院業務規模逐步擴大和把營運走入穩定。
後來才陸續加入了婦科、小兒科、和內科等科系。醫院規模才正式穩定,病患也從煤礦工人逐漸增加到基隆市民,甚至遠至台灣北部的漁民、碼頭工人也都來此接受醫療,也由於醫院科室的增編、自費收入增加、病患來源增加,讓醫院營收也跟著增加,營運狀況也變得漸入佳境和穩定了。
我個人在七零年代時接觸了廣大的漁民、碼頭工人、礦工等人後,讓我更加了解台灣北部勞工大眾們的真實生活及需求,對於我日後從醫生涯中、有了很大的啟發和影響力。而對於來看診的病患,不論是屬於一般大眾的平民百姓或是達官顯耀、巨商富賈等人、我都能如Hippocrates誓詞、視病猶親般的一視同仁對待。
在七零年代,對於所謂腰脊柱狹窄的觀念並不普遍,當時尚未有MRI設備,CT在台灣還只是一種新觀念,大部分的背部都是以腰椎顯影液作為診斷的依據,因此,很多診斷的疾病、都誤以為腰椎間盤脫出症(HIVD)。後來在我廣泛的涉略文獻後,才知道有所謂神經性跛行這個名詞。事實上在1976年,國外文獻中才正式有腰椎狹窄症病變的新觀念。本人也很榮幸,以礦工醫院的病例中、報導並在「台灣醫誌」刊登第一篇的「腰椎狹窄症」病變的文章。這段期間,我也陸續寫下並發表有關「腰椎疾病再手術的病例評估」的文章。只可惜,本人對於當時對脊椎受傷的治療成果的經驗,尤其是以哈靈頓桿的整復方式的經驗,未能及時發表一直引以為憾。
在礦工醫院任職期間,也多次自掏腰包前往歐、美、日等各國觀摩髖關節手術的治療,常常弄得毫無存款,但也因此我陸續也做了一些病例報告。在礦工醫院這六年當中,一直專注在做髖關節重建和脊椎手術,這二種的手術一直是我當時的最愛,也最難以抉擇我未來的方向,我知道魚與熊掌是難以兼顧的。
礦工醫院在當時贏得台北各大醫學中心的贊許。有一年,中華民國骨科醫學會竟挑中礦工醫院來舉辦外科醫學研討會,我記得當時的理事長盧光舜教授率領一批榮總醫師和三總施純仁教授、台大醫院許書劍教授、陳漢廷教授等人把小小的礦工醫院擠爆,那天我的心情真是既興奮又驕傲,但也是五味雜陳、百感交集。另外還有一次,台大邱仕榮院長、長庚張錦文執行長二人同時率領醫界的龍頭,到礦工醫院召開醫院協會之理監事會,在此小廟能承蒙醫界大老多次青睞和看重而願意遠來此召開會議,讓我們及這裡的全體員工皆感振奮和受大很大的鼓舞力量,間接也是對我們年輕人的一種鼓勵和肯定,誰說不是呢。
1978年6月間,在台大外科和許書劍教授指引下我返回台大醫院服務。回憶起六年在礦工醫院的經歷和經驗,不論是在學術上、為人處事、學養見識、醫療技術及養成技術上…,在在都是我此生最值得珍惜和回味的歲月。這些曾經一同工作的礦工醫院的夥伴們,日後都變成了我一生最要好的朋友,我也深深感到醫院裡的每一位病患,都像是一本珍貴的教科書,讓我從中可以領悟和學習到許多醫學的經驗。當時醫病的和諧關係,更令我堅定志向,願意終生為病患服務。而這種類似史懷哲的精神,也不是微薄的薪水可以用衡量或取得平衡的。
四、台大外科的生涯
記得有一位前輩陳秋江老師當面告訴我:「人生每一個抉擇都像是三叉路般行走,其實你在礦工醫院的工作相當成功、而且彌足珍貴,而你願意拋棄它而重回台大從講師做起,對你個人是一種損失」。我記得當時我回答:「確是如此。」因我考量在學術上還有進步的空間,回到學術殿堂工作,肯定可以彌補未來可能的損失。陳秋江老師神色淡然的對我說:「我可以了解你的心情,但是一旦決定就不要後悔」。我就真的回到了常德街一號。窩居在一個黑暗的研究室裡,與廖廣義和劉華昌醫師三人一起分享那有限的空間。
少了醫療行政業務的繁瑣工作,但卻增加了教學與研究的壓力。此時骨科病房也由一西病房搬到十三西病房(原來的美國海軍研究所的房舍) 。事實上,骨科在當時只是外科的一個小單位,真正屬於骨科研究的空間與設備卻付之闕如,而當時陳漢廷教授已生病,大家的士氣是悲傷和鬱抑的。
當時政府的預算大部分都編列給台北榮總,而身為台大院內的醫師和領導,心中都是有一些憤憤不平的感覺。記得當時黃煌雄立委也深感這種分配不公的情形,在立院質詢中也特別提出,並要求對台大醫院更新設備經費的提高。這種聲音漸漸受到社會輿論和政府注意,後來蔣經國總統聽到後也接受請求,並指示政府增加預算、所以當年台大醫院楊思標院長得以取得改革開始的進一步,而台大醫院的設備才漸漸擴充。
我個人一直覺得自己學養俱不足,難以做更高深的服務,尤其是脊柱手術充滿挑戰感、乃興起想赴美國進修的念頭。當時得到外科洪啟仁主任的同意和鼓勵,並於1982年決定到芝加哥攻讀一年。事實上,我仍然在關節重建和脊椎醫學二者的領域中徘徊,難以取捨未來專業的抉擇。
幸有郭耿南學長的幫助,我幸運進入芝加哥老長會醫學中心(Presbyterian-St. Luke Medical Center)進修一年,當時這家醫院骨科有髖關節 (Jorge Galante)及脊椎側彎專家(Ronald L DeWald),當時兩人都是美國骨科界著名的學者,我最後終於圓了我魚和熊掌的選擇。
同時期,台大醫院為增加醫師名額,楊思標院長徵得了許子秋署長的同意,要派遣醫師到沙烏地阿拉伯從事醫療服務的工作,如此政府願意給台大醫院壹佰名主治醫師的名額。這是當時中沙醫療團成立的源由。當時張錦文是「中、沙醫療團」的團長,台大醫院謝炎堯是副團長,因此從1982年起,台大才陸續有一批醫師、護理、行政人員到當地沙烏地阿拉伯的東部霍夫(Hofuf)醫院服務。楊院長希望有幾位醫師當醫療團的顧問醫師,而顧問團是由劉楨輝醫師帶領,旗下有許光庸醫師、侯平康醫師及本人總計四位,而我是最年輕的一位。我們比第一批晚了三個月到達。我因為考慮七月要到美國留學,不知如何是好。有一晚楊院長邀約我們四人到他家裡用餐,我記得當時是初春三月,在楊院長的府內三杯黃湯下肚,就這樣決定了我去 Saudi Arabia「中、沙醫療」的行程,原來預計顧問團要六個月,但我特別拜託而得以只停留在沙國三個月。
五、沙烏地阿拉伯三個月的生活
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和制度下工作,實在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歷練。全體在沙國東部省Hofuf的醫療團員,加上眷屬共有三百多位。醫師們住在有警衛的營舍裡。這段期間,大概是我一生行醫中最悠閒的日子。一個人住在約卅多坪大的獨立房子、每天晚上開著免費的冷氣。但用水則是淡化的海水。三餐都由院方供應,完全不必花腦筋。院區內有游泳池舒緩筋骨,周末有韓國人來放戶外電影。偶而當地人也會請我們去品嚐全羊大餐。連烈酒也可以喝到,真是享受之至。白天上班並不太忙。我主要工作是手術。在三個月內作些total hip replacement,小孩DDH的 Salter reconstruction procedure,脊椎的手術也不少。這些病人都由副院長 Mokaya及一位埃及醫生準備。也因此當地報紙也刊登幾次本人的成就,可惜阿拉伯文無法閱讀而沒有剪下來保存。我也診斷過osteopetrosis遺傳病及vitamin D deficiency引起 ricket的小孩。前者是遺傳性而後者是沒曬太陽造成的。如今想起這段日子還真是挺有意思的,尤其是夜晚靜坐在高低蜿蜒的砂丘上,遠看孤寂的月亮高高掛在黑暗的天空上,那種感受只有在唐詩的意境中才可以感受到。如今政息人散一切都不再可能再來一次。
六、芝加哥一年生涯
芝加哥在美國是屬第三大城市,座落在Illinois湖西。也是美國中西部的工商企業的中心,這裡的醫學也相當發達,長老會醫學中心是附屬於Rush大學,也是學長郭耿南教授服務的工作地點(負責小兒骨科醫學)。郭教授在當地也是位名醫,在其介紹下認識了Jorge Galante主任,他是位人工關節手術置換的專家、當時正努力於Cement-less fixation。另一位Ronald L DeWald教授是屬於脊柱外科手術專家,尤其在脊柱側彎的矯正和脊柱癌轉移的整復(reconstruction)上、特別有心得。我能在此學習一年,內心充滿了期待。我希望在這一年進修的期間,可以得到新觀念和新知識,更期望回國後能貢獻其所學。
當時美國的法律還算很寬鬆,我可以跟著老師到開刀房參加手術和從事助理的工作,並且在門診中與病人實際參與診療互動,當時人工關節的發展除了以骨水泥固定正在進行,不必以無水泥固定方式。Galante教授研究使用細小的鈦纖維片貼附在人工關節的表面上,鈦纖維孔隙太小約在30-150μ的範圍,此範圍適合骨細胞的長入,所以是一種生物性的固定法。這種方法基本上在人工關節植入的初期必須牢固在關節內。我的工作就是參與動物實驗。當時我在伊利諾州大學的大型動物實驗裡用了三十多公斤的大狼犬作為手術實驗的對象。
這間動物手術室的設備很新穎且齊全(與台大醫院新的手術房相當),所以除了狗以外,尚有大型的動物,如:牛、羊等都可以在此做實驗性手術。令我印象深刻的工作夥伴中有一位獸醫師(Dr. Tom Turner)、他的動物手術很內行,也是任職芝加哥動物園。他的身體胖胖地,臉上永遠帶著笑容,我和他以及骨科實驗室管理師(Bob Urban)、我們三人是一起在手術室工作的夥伴。以狗做Canine THR、術後都沒有留下任何的合併症,手術非常的平順,每至一段期間 (三週、三個月乃至六個月)我們會將手術實驗的大狗的腿部取下,為其拍照X光片,另外又將植入人工關節的狗腿分段切開,其薄片經染色後觀察骨細胞長入鈦纖維片(sintered titanium fiber)的程度並做量化,同時也觀察骨皮質部分(cortex)置入人工關節後的反應如何。因此,皮質骨部份空隙有多少,也是我需要觀察與計算的目標,這須透過電腦來測量。這是一個相當繁瑣的工作,每日要用顯微鏡來觀察,讓我的視力很受損以及常常使之眼花撩亂,而且主要是因彎腰駝背,搞成腰酸背痛。這份努力的研究、後來刊登在CORR。幸好當時有郭耿南教授及夫人的幫忙照顧,讓我的身體得以充分休養以及視力的恢復,也因長期工作的疲憊而讓我之後飽受腰酸背痛的折騰。在這以前,我是一個很喜歡運動的人,也幾乎把運動當作生活中重要的休閒活動,但自從來美國芝加哥見習後,我不得不捨棄我最愛的運動了。記得去年報上登個消息、說某位愛狗人士、為心愛的狼犬作THR、手術費用要價台幣二十萬、比健保給付給人做THR的價格還貴、看來我應該可以考慮改行做獸醫。
芝加哥也是一個文化中心,我只要一有機會一定會到當地的美術館 (Chicago Metropolitan Museum)和(Marshall Field Museum)博物館等兩個地方參觀和流覽當地的收藏。前者收藏印象派畫家的作品甚多。而 Marshall field博物館館藏非常豐富,有很多史前恐龍骨的自然博物典藏。在芝加哥當地有很多的富豪都勇於捐贈,裡面也收藏了有許多西藏的宗教典章與中古歐洲兵器。這裡真是一個美麗又深具富饒文化知識的好地方,如果有機會來此一遊,千萬不要錯過,一定要記得去這兩個地方看一看。
另外,這裡的Chicago交響樂團和歌劇院也頗富盛名,我有時興緻一來也會前往參去聆聽觀賞,只是這裡的時間不太允許我,讓我有很多的時間在此二個地方盡情享受音樂的洗禮,現在想想卻深感可惜。倒是夏天夜晚、在湖畔也常有露天的演奏、免費提供市民的消遣。芝加哥的四季分明、風景秀麗,經過一個寒冬的洗禮後,處處可見枝頭上展露出春天的氣息、由新發出的嫩綠新芽,翠綠轉青綠再變成綠樹成蔭的大樹,這是身處在亞熱帶四季不明顯的台灣很少見的情形。
我覺得現代的年輕人已比當時的我們好多了。如果有機會,一定要四處旅遊、走走看看,並參觀比較各國的文化差異與不同,讓自己不僅可以提升視野,也可以增廣見聞,更可以藉此來磨練和適應這個複雜又多變的世界。可惜,我當時來此已年近四十歲,而且當時的規定不能攜帶眷屬(國科會不允許),我在此生活,離鄉背景、暫拋妻棄子的情形下,孤單地在此停留學習,心裡充滿的鄉愁與對家人的思念,每每在夜深人靜時,更加備覺感傷與遠離的悽涼。
七、1983年返國工作
我於1983年8月初返國。當時台大醫院骨科內的主治醫師只有劉堂桂教授、韓毅雄副教授、以及我和劉華昌講師。返國後不久,劉堂桂教授即指定我在脊柱外科上做進一步的服務,我也欣然接受並且明白地表示,從此不再從事人工關節方面的文章發表。我這一路走來,脊椎外科與我相伴已有二十五年之久,直到我現今退休。
事實上,回國後來看診的脊椎外科的病患不多,影像診斷的工具尚停留在普通的X光片及Myelograms,能使用的脊椎固定器當時也只有哈靈頓桿(Harrington rod、中國大陸稱哈氏棒),早期我還在礦工醫院服務時、即有相當的使用這種固定器械的數目。但大部份仍使用William plate、它固定著 spinous process、這種方式當然不夠 Stable。雖然當時的設備和診斷器具尚屬簡陋,但在劉堂桂教授的指示及支持下成立了特別門診,當時的名稱、原本想命名為「脊椎外科」特別門診,但有一些神經外科醫師有意見反對,因此改為「脊椎側彎」特別門診。而時間訂於每週四的下午作門診的時間。承蒙大家的厚愛與病人的支持,此門診漸獲認同,因此病人的數目和各類脊椎手術項目也都逐日在增加。
在此門診中、常有各種脊柱畸形以及頸、胸、腰椎之各種脊柱疾病的患者前來求診。當時工作量早已超出我個人的能力負擔範圍,門診中除了一至二位的護士外,沒有其他人的支援,當時骨科還隸屬於外科中的一個單位,因此想尋求奧援幾乎是不可能。其實這是 Solo practice、要不是有一股傻勁、真也想要拍拍屁股走人了事。
在80年代、甚至到今日,脊柱外科的成長非常的快速、且多樣化,醫生對脊椎疾病的認識以及治療方式也產生了革命性的轉變。由於矯正器材的研發和實用,也由於診斷工具的明朗化,使得過去不可能的手術變的可能了,使過去療效不佳的治療方式也變得療效更佳更可靠了。這些的改變真可謂是醫療革命性的改變啊。
舉個例子來說吧,過去脊柱側彎的手術是用單根哈靈頓桿矯正及固定,病人還需包上厚厚的石膏背架,把身體裹緊,少則六個月,多則一年。尤其在台灣炎熱的夏天裡,真是難以忍受的,夏天裡無法洗澡,對青少年來說實在苦不堪言,而對於醫生的我和家屬也是感同身受,且只能抱以憐憫以及同情心的無奈。
我於回國以後即利用哈氏棒和路氏棒(Luque rod)兩種的結合,讓彎曲的脊柱在每一節裡都有鋼絲的纏繞,讓手術的結果和讓原有手術的矯正率由40%上升到60%。從此病人不需要再包石膏,此一固定的方式比原先的傳統方式變得更加牢固,小孩子只要穿上樹脂做成的背架即可,且時間只需穿戴三個月。病人也因此可以洗澡,也因療效大為改善、家屬更能接受手術。因此,門診的工作更得到病人和孩子的認同,醫療業務量急遽增加。後來這種矯正用的植入器材又有了新的轉變與改進。比如法國的CDI就是以兩根金屬棒依靠鉤子連結在多節的畸形脊柱的兩旁,同時利用棒子在脊鉤間旋轉來改正畸形的椎節、而非撐開椎節。因此,整個脊柱的固定更加穩定,同時也可達成脊柱三面畸形的矯正,可以以一次手術的達成,當然也不再使用包石膏的方法。因此很快的風靡全世界。為了學習CDI法,我也到法國親自向Cotrel先生、Dubousset先生以及蕭邦(Chopin)先生請益,這些醫師多年以後都仍是我的好友及摯友。自1988年起、大致用了260例以上的Scoliosis 治療吧!
對於能在大醫院裡工作、可以為廣大病患服務、也可以和許多年青醫師聚會、教學相長一起學習和研究、也可以和先進前輩醫師一起共識,這種種組合,遠比財富的累積,和空有的名望,對我而言是比較有意義的。因此,即使工作相當忙碌,我也習慣、也可以樂在其中、達成當年回母校的原意。
在當時倡導前方(路)手術有一位德國Zielke醫師、他設計一套固定在前方椎體的器具名叫VDS。它是一種可以讓腰椎的畸形得到良好矯正及固定的方式。Zielke先生和夫人也曾多次來台灣訪問,而我也曾多次前往德國請益,大家非常熟識,我不但以VDS來矯正脊柱側彎,同時也以用在病人的駝背手術。駝背手術是台灣最常見僵直性脊椎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病人利用的脊柱手術之一,駝背對一個人在生活上很不方便,因此這種手術是有其必要及重要性。今年 Thieme公司新出的 Surgery of the Pediatric Spine 一書、就有一篇相關文章刊載。這是80年代中期之後時期很進步的一種手術。後來椎弓釘(Pedicle screw)的使用漸漸普遍,我就是利用椎弓釘的使用,將椎弓釘經椎弓孔穿入椎体,用以治療駝背。
後來脊椎的手術治療又變得更加五花八門、不勝枚舉、我真是恭逢盛世。因此到了1988年,我們認為有需要設計一套使用上更方便、手術器材種類更簡便、而且能固定在脊椎上不容易鬆脫的骨釘,於是我展開了一段辛苦又漫長的研發工作。實驗與研究的展開,包括豬脊椎骨的實驗、人屍的模擬以及生物力學測試等等。從1988~2000年,我們陸續有一些工作的團隊,譬如:署立新竹醫院的施啟明副院長、王子康醫師、工研院趙偉泰組長的研究群、後來又加入鄭誠功博士、三總骨科吳興盛主任、台大機械所蘇侃教授,以及一群的研究生,例如林上智博士等、和台科大機械所趙振綱教授以及其學生等等的協助與合作,開發一系列新型脊椎固定器。其中也獲得國科會的財力補助,讓我得以順利地完成。目前這一系列自行研發的Formosa Implant,委由本地公司製造販賣,可以當做各式脊柱毛病之手術用,我不敢說這是一件多麼了不起的工作,但是可以親眼目睹國人自製研發的醫療器材、用在病患的身上,而且受到歐美國家的專家學者的肯定和贊揚,我內心的喜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的。國父曾說過:「主義是一種信仰、思想和力量。」我也深深體會到一件產品的誕生,也是由一種原始的思想然後去改良設計而達我。在病人的身上我完全得到了良好的印證,這其中的成就,實在是無法用金錢來估算的。尤其是自製研發的產品、不但可以使用在臨床上時,可以感受到病人的肯定外,還可以使國家外匯的增加、國人就業率的提升等等。這都是對我身為一位醫生的我,對於社會在實質上最有意義的一個貢獻吧。同時每每看到年輕醫生在我們的教學及督導下快速成長與茁壯,內心的甚為寬慰。年輕後輩們長江推前浪,前仆後繼的優秀表現,這也是當醫生和老師的我另一種喜悅吧。

左一為陳博光教授在台大醫院實地教授學生了解脊椎之情形
之所以把精神和心力用在新型器材的研發上,其實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上。記得在某一個夜晚,我載著陳博約教授回家的路上,車停在老師的家門口,老師似乎有感而發、突然地告訴我:「你的手術做的很好,且國內的醫材都是國外進口來的,還有很大的空間值得改進的地方,你可不可以利用時間去改良並突破。」老師的這一席話在我的內心逐漸發酵,並形成我創新的一股動力。當時應該是為某位政要共同完成手術之後吧。其實每每有國外的醫生報告他們設計的人工關節器材有多好多好後,我們台灣的醫生也在使用後發表認為也很好。但當我發覺國外醫生在談論使用的醫療器材很好的同時,國外的廠商又已著手開始研發新的器材了。我覺得談論它們的好與壞沒有太大的意義,只是在做拾人牙慧的工作,我們缺乏「原創性」的東西。
隨著台灣經濟的起飛、社會醫療品質要求的提高,我們醫生的水準也逐漸在提高。因此,90年代的時期,喜見新一代的骨科醫生逐漸的茁壯,骨科醫生遍及各大醫學中心,也因為這些更堅強陣容有更完整的訓練與學習機會,因此骨科學也就更加蓬勃發展和成長。這也是我內心中另一層面的喜悅的成就感。我們希望這種不停的研發與創新的意念能夠不斷地向前駛進,並期望有一天能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進而促進國家經濟的繁榮,與社會民眾的福祉,這實在是我最大的心願了。
八、APOA參加醫學會的感想
作為一個大學工作的教員,除了教學、研究和服務以外,另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與國外同行做雙方多重地溝通,也惟有在這種學者互訪和國際會議的場合中,我們可以更快速和深切地了解到別人的研究進度和實質研究內涵。說實在的,與同行談起互相研究,可說是「華山論劍」般的一種方式。病人要求的是要你能力的付出,學生要求的是知識的傳授,但是同儕的交往才能促使你做更深入的研究和自我成就的提高。打從我進入台大醫院從事教職工作剛始,這種思考即一直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腦海中盤旋。
就以APOA(亞太骨科醫學會)為例吧。早在1976年時期,由陳漢廷教授擔任我國代表,帶領幾位醫師前往韓國漢城參加WPOA(西太平洋骨科醫學Western Pacific Orthopedic Associations),它是APOA的前身,於2001年改名為Asia Pacific Orthopedic Association, APOA)。當時的會場不大,我可以與來自各地的學者專家齊聚一堂,一起參加醫學會議,在當時的確給了我一個很大的震撼,我稱它為「東方的震撼」。是有別於參加美歐醫學會的感覺,那是「白種人的震撼」。沒想到東方的學者專家也同樣具有別有一番的見解,非常有意義。會後我們到日本札晃開會,我也更親近的接觸到幾位有名的脊椎的手術專家,其中有如香港大學的邱明才教授,他流利的英語表達、精湛的手術示範,深受日本骨科界的尊敬。之後我還跟他到東京。東京大學的津山直一教授特別租一家大飯店的講堂裡舉辦了一場學術演講會,他當時演講是脊椎側彎手術的講題。另外還有一位是馬來西亞的Silva教授。當時年輕的我看到一個如此美妙的演講會,心裡有了極大的震撼,也開始更堅定的告訴自己,一個人一定要做到出類拔萃,它也正式開啟了我對此會的濃厚興趣。
目前APOA共有十九個國家。原先包括日本、韓國、台灣、香港、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澳洲、紐西蘭、泰國及越南等等。自2001年在澳洲Adelaide開學會、改為亞太骨科醫學會(APOA),同時再加上了印度、中國、巴基斯坦、鍚蘭、孟加拉及土耳其等。由於台灣的骨科醫師們在各個學術會議中,均有主動而又具有優良之表現,一直備受各國醫師之肯定。
APOA於l979年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辦第六屆醫學學術大會。當時由國防醫學院鄧述微教授擔任會長(理事長),由台灣大學陳漢廷教授擔任學術會會長。總幹事由尤耿雄主任擔任,財物長則委由我擔任。這是我第一次能夠參與以及目睹其整個內部運作的國際會議,對於我個人的生涯也有很重要的影響。由於我國之前從未有過如此大型之醫學活動,來參加之國內外的醫師有三百五十名以上。因此,內政部特地頒發獎狀及獎金壹佰萬元,用以鼓勵骨科界對國際學術之交流與增進我國醫學水準之提高。政府用心可謂良苦,我們是充分的感同身受與有榮焉。而當時骨科界同仁的努力,其中還有何亨基及馬擢前輩們的付出、梁鉑鈴、施俊雄等的付出、亦實不容?剎。近些年來,骨科醫生均能夠主動並積極地參與這個學會的活動。
由於醫學的分工變的更加細緻、並以次專科的方式為病友服務。而脊柱外科又是AP0A架構下之強項。因此各國脊柱外科之前輩們,乃率先成立了Spine次專科,以加強訓練各國脊椎外科年輕醫師,並相互交流以便提高醫學水準,進而為病患服務。因此在1982年成立脊柱外科分會(Spine Section, APOA)。
Spine Section, APOA是目前 APOA所有分會中最悠久最堅強的中堅分子。由於和小兒骨科關係密切,故後來的學術活動都一起辦理了。除了有定期的學術會議外、還有一項實境手術示範。學會邀請專家們、在不同國家手術及講解、希望有志的年青醫師能捉到重點、早日學會手術。這是世上僅有的一項活動。本人多年來不但榮膺指導教師、也負責安排之重任。
自1986年起,我們在台北一連舉辦四次國際脊椎研討會、邀請國際知名學者來台與國內同好交流。這對提高國內 Spine水準有一定的貢獻。近些年來,鑒於要提昇台灣骨科的能見度與高度,以脊椎醫學研究基金會(Taiwan Spine Research Foundation)的名義,也在台灣舉辦幾次國際性醫學會議。如2003年12月5~6日假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APOA亞太骨科北區醫學會,當時敦請嘉義長庚醫院許文蔚副院長擔任學術大會會長,熱鬧空前辦了一次「2003年亞太骨科醫學會議」。並於2005年於11月22日~25日因當時擔任台灣生物力學學會理事長,並也舉辦了「第二屆亞太生物力學學會(APB) 」地點:台北福華文教會館。來台參加的國外生物力學之專家學者有150位,而國內參加者有230位。接著於2005年的11月24日至27日也舉辦「第六屆脊椎外科暨小兒骨科聯合會議(APOA) 」。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計來台之國外學者達350位。
我於2007年9月期間前往韓國首爾,正式接任APOA會長一職,任期是由2007至2010年。預定2010年11月、將在台北舉辦APOA的年會。距1979年在我國開會、已整整卅年。昔日主辦的骨科前輩、均已經離開我們。多年來的參與國際會議及付出,我終於能看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茁壯與欣欣向榮,未來該是年青一輩要傳承與接棒了。我很樂見現在的年輕醫生能熱情與主動地參與國際醫學會議,相信不久的將來,台灣的高度與能見度一定能夠再次展現開出豐富又美麗的成果。

2007年9月陳博光教授前往韓國首爾,被任命擔任(2007-2010年)APOA大會會長,此為當天會場手持會旗接受大批媒體拍照之情形。
九、與國際骨科之接軌和連繫
由於經常到國外參加學術會議,不但在歐美場合,也在亞洲各國經常列席。在這些場合常常會遇到來自不同國家的專家們,一面吸收新知、一面認識朋友,也可以同時了解別國學術進展的情況。同時也因為自己有上台發表論文、參與討論,無形中增加知名度與對台灣的認識。一般而言,美國的學會較有競相表演的氣氛,且水準頗高。歐洲的會議常有新觀念出現。日本韓國的會議中規中矩,很有水準。東南亞的會議可以感到愉快的氣氛。近年來中國的醫師的努力表現,水平提昇很快,希望我們年輕的一輩要多多努力,尤其在醫學中心的同仁,更有責任主動參予。今年六月將在濟州島舉辦的spine會議,主辦的韓國教授就要我推薦三位台灣年輕醫師分別參與頸椎手術、脊柱外傷及研究三個 symposia。本人就分別推薦大林慈濟醫院簡瑞騰、長庚醫院范國豐及台大醫院楊曙華三位醫師分別上台發表。今年五月日本整形外科年會我也鼓勵蔣建中醫師參加,他以血友病人之 TKR台灣經驗一文參與比賽,獲得獎金並將上台講演。該文章也獲 「Haemophilia」 雜誌接受刊登。蔡文基醫師也曾獲邀到日本脊椎學會講演。其他就不再一一敘述。我要求的是我們的年輕一代不可以在學術界中缺席。
也由於近來在各種學術會議中屢屢曝光,因此各國年輕醫師也興起來台灣見習的風潮,這幾年陸陸續續有近五十名的外籍醫生前來。即使美國以及日本的學會,都有主動派人前來台大醫院交流的趨勢,並做短期 fellowship。個人能力有限能做的儘量去做,相信年輕的一輩會更有成就,在學術上為台灣更增光彩。幸好有「台灣脊椎醫學研究基金會』在財力上支助,才能夠讓一些外國醫師們順利來台大進修。台灣脊椎醫學研究基金會創辦迄今已十餘年,獲得社會大眾的捐助得以在學者交流、與舉辦學術會議和發行學術刊物,例如Journal of Musculo-skeletal Research, JMR以及龍骨雜誌和網路www.taiwanspine.org.tw) 提供各國學者發表論文,以及提供最新骨科新知給一般民眾的醫學資訊場所。因此,本基金會也多年來被評定為全國三百大基金會之一。

此為基金會十週年慶,眾貴賓在陳博光董事長的帶領下開香檳以示慶祝
歲月悠悠,不知不覺中我也從意氣風發的青年,轉變成白髮蒼蒼的老人。歲月不饒人,於今所企求的僅是身體健康、生活平靜。所願者是台大年輕的骨科醫師能夠腳踏實地做學問,有朝一日能夠角頭崢,與先進國家的專家們共同砌磋、平起平坐、並發揚母校榮光。
十、後記
本人無多大能力,能屆齡退休已了無遺憾。退休時,承蒙科內同仁舉辦退休學術會以及惜別晚會。在這聚會的場合中,能與多年來未曾謀面的老友相聚一堂,尤其是林榮一學長抱病參加晚會。又有我的老師及校友們、血友病協會會長、沈銘鏡教授、院內長官、都在百忙中趕來參加,內心感到非常溫馨、非常感激。
在此,也要向很多花時間為我工作的同仁,如骨科江清泉主任、楊曙華、徐錫靖、張志豪等醫師、黃千小姐、以及很多住院醫生的助理們,我無法在此一一列舉的同仁們致上我無限的謝意。沒有大家的奉獻,這本冊子以及難忘的活動,肯定無法完成。
陳博光 寫於2008年4月初。
台灣脊椎外科之父陳博光